文|理想国imaginist

这些年,“抑郁症”成为公共话题。主页君身边,也不乏例子。偶尔与朋友讨论到这话题,常会出现静默悄息的片刻,言语俱废。
太沉重,它像是深渊,凝视着我们。或许在这个高压、急躁的社会,人生艰难成了共识,但在艰难之下如何来去,每一个人都需要反复思考和确认。
......
今天微信,分享一个独居的抑郁者如何与之对抗的日记,选摘自梅·萨藤的《过去的痛》。
她在日记中坦诚了人生中的两段艰难时期:66岁,伴侣患上阿兹海默症,她痛失所爱同时深陷抑郁,还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73岁,她又不幸中风。
梅·萨藤写得坦然、平静,不遮掩精神的焦虑,也不讳言身体的弊病,而是深入地思考自身与过去的关系,在自然与日常生活中得到从容的奥秘。
她说:“打击唤醒了隐藏的力量。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
1.
1978年12月28日
星期四
关键词:诗歌
一个奇怪的没有温柔的圣诞节。甚或只有陌生人的温柔,因为我收到了大量关于《报应》的信,有几个人还恳求我再写一部海边日记。
“它们仿佛是特别的礼物,有助于我生命的恢复……对于我,你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
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当我偶然翻到《诗刊》(Poetry)十二月号中威廉·海因(William Heyen)的这首诗时,那真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
《田野》
每个圣诞前夜,外面
黑色的田野中,雪在孤独地闪光
我合上双眼:很快
那字迹再次出现
死榆树和栗树的根须
在地下,发红
这词语永远不会消失
我的朋友们——似乎我们并不知道

梅•萨藤(May Sarton,1912.5.3——1995.7.16),美国日记体作家、小说家和诗人,创作了二十多本小说、二十五本诗集和日记。
2.
1978年12月29日
星期五
关键词:痛苦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所谓的“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他每次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
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莱特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此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

梅·萨藤晚年独居于缅因州的约克,也去世于此
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过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
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保利娜·普林斯(Pauline Prince)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有时的我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
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都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的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
3.
1978年12月31日
星期日
关键词:新生
温柔是心灵的优雅,正如风格是思想的优雅。
昨夜我不能入睡时得出了这个结论,两者都与质量有关,感情的质量,理性的质量。

梅·萨藤的猫和狗:塔马斯和布兰波;梅·萨藤十分喜爱动物。
对我而言这是艰难而痛苦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期盼明天的黎明,当白昼变长,我开始摸索我进入新生的路。我们的“新年”在季节轮回最黑暗的时刻来临,这虽然神秘但并不陌生。
在个人的黑暗存在的时候,在有痛苦要克服的时候,在被迫更新我们自身来对抗所有反常事物的时候,单纯求生的心理拥有巨大的力量,大得就像一个球根顶起春天冰冻的土地一样,于是在克服困难之后,就会有额外的能量,会有可以投入创造的一股能量的洪水。今天早晨我开始写作一个中篇小说,事实上,从上个夏天起,有几个月它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4.
1979年1月5日
星期五
关键词:“康复”
现在最糟糕的是我不再有任何遥远的希望,任何我可以用跃动的心去期盼的东西。过去这一年我丢失的是使命感,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作为一个爱着的人我必须贡献的一切,或者作为作家我所出版的大量作品是有价值的……
这种价值意味着所有投入爱和作品中的奋斗与痛苦没有浪费。说白了,我就是感到自己失败了。老得不敢期望事情会变好。我以如此残忍的方式被“放倒”了,只有凭顽强的自我考验才有可能康复。而且这并不是真正的康复,只能说是活着。做一个作家,因为技巧是我唯一可以操纵的东西。我仍不能从去年发生的一切中“康复”过来。
一条轨道,我拥有自己和我的力量的感觉,已经碎裂了。

梅·萨藤1973年隐居后沉思、写作,不断体悟人性中最难克服的孤独。
5.
1979年1月11日
星期四
关键词:感情
美国人的气质允许人向动物表露感情,却常常阻止向同类的表露。是害怕失落吗?还是以为表露感情,尤其是流泪,是软弱的表现?
今天我提出这些问题,以前也常常是这样,我想起有一天在《时报》上看到过本杰明·布莱克(Benjamin Blech)的一段话,他是纽约州的一个拉比(1978年12月31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他说: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桩罪行而哭以及感情的表露是最羞耻的失败?我确定不了其中的原因。但我知道克尔凯郭尔是对的:我们的时代缺乏的不是沉思而是激情——我们为不可计数的痛苦和灾难付出了代价。
也许,我们都以一种哲学观念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指的是判断我们的天性。我是个非常开放的人,易感并能够表达感情,经常会哭(顺便说一句,布莱克文章的题目是《哭,请哭吧》[“Cry, Please Cry”]),并对这种天性毫不怀疑。我们都浸淫其中的美国清教徒气质,强调自我控制是最高的美德。感情是无政府的,能够冲毁栅栏,那可能带来危险。哭泣是女人的事,意味着软弱,缺乏自尊;因为自尊意味着控制,甚至是自足。流泪几乎总是为寻求帮助。
布莱克接着说: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我们认为我们对待软弱的方式是自然的,我们甚至继续将热情与不成熟混淆起来……在热情的承诺能最好地表达爱与关心的时候,为什么理想的反应一定要“酷”?

年轻时期的梅·萨藤,她与同性伴侣朱迪共同生活超过了十五年。
布莱克后来引用了怀特海的话:理智之于热情正如同衣服之于我们的肉体;没有衣服我们不可能过上很文明的生活,但如果我们只有衣服而没有肉体,我们将非常贫困。
布莱克又继续道:我们时代令我悲哀的是,人们对感情的自然流露所采取的不自然的轻蔑……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耻于承认,每当我看到自我控制的榜样时,我总忍不住为他们哭泣。
也许一个人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承认自己的需要,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6.
1979年1月12日
星期五
关键词:孤独
因为我独自生活,最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所以我在孤独中写作。
但这些天来我逐渐意识到有两种人对我的作品极感兴趣——首先是生活孤独的人,她们是寡妇,她们的孤独是“既成事实”;而第二种,是还没有对生活做出承诺的年轻人,既在工作也在爱情方面——对于后者,我这个榜样可能是有害甚于有益。
我已经逐渐成了孤独生活的代表,这选择本身在对抗婚姻或生育方面是有效的。也许在人的一生中确实有两个时刻,二十岁和六十岁之后,孤独能带来创造。
但对于两者来说,只有二十岁时孤独才是一种选择。并且这几乎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选择,因为生活在继续,有各种可能会改变生活的进程。
如果一个人确实选择了孤独,那一定有某种目的,而非仅仅是为了寻找自我;探索“个性”是这些日子的一个时髦概念,但有时至少显得像是纯粹的自我放任。
一个人如何发现自己的个性?我的答案是通过工作和爱,两者都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都需要克制、自律以及一种无私,并且都是毕生的考验。

梅·萨藤虽未婚无子,离群索居,却为独居者们展现了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
7.
1979年1月13日
星期六
关键词:工作
做菜的时候我想着那个憎恨做妻子和母亲的女孩,因为她仅仅清晰地看到了那样将有多少家务事要做,她把母亲看成一个应该同情的囚犯。这些日子接受这样的态度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么多为人妻和为人母的女人在遭受挫折,上帝知道。
但有些时候我反感拒绝负责任拒绝尽义务的论调(仿佛一个人真能如此似的),反感将养育儿女看得不值一顾。家务事的麻烦当然在于它是重复性的。吃完饭你要清理餐具,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

梅·萨藤坚持写作几十年不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但这些年轻女人似乎忘记了每一种工作都有惯例的一面,都会有挫折和空虚。学生从未想象过自己的老师要花多少时间来写那些无止无休的建议,或是准备一个讲座时那绝对艰苦的工作。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正因为这样,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付出了。
伹有些人仍在工作。我想起玛莎·惠洛克(Martha Wheelock),一个素食者,她能花几小时把蔬菜摘好,烹制美味的饭菜,她说她可以一边做事一边沉思;而且她过的是忙碌的职业生活。有人看到了烹饪和家务活有圣礼的一面。例如,把干净的单子铺在床上。事实上,随时随地把混乱整理成有序,都可以看作一次圣礼。
|
图文选摘自《过去的痛:梅·萨藤独居日记》
梅·萨藤 著 马永波 译
理想国,2016.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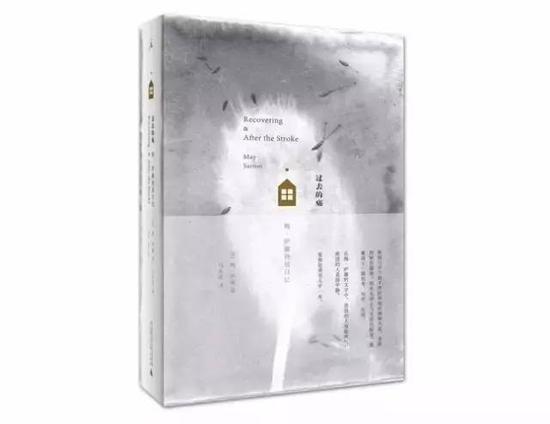
特约编辑:张舒婷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