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大外文学堂
达马索·阿隆索(1898—1990)像他的好友萨利纳斯、豪尔赫·纪廉一样,也是杰出的诗人、教授。
他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富裕家庭,在加利西亚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19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法学院,是著名学者梅嫩德斯·皮达尔的得意门生与合作者。1921年发表第一部诗集《纯诗:城市小诗》;1924年出版《风与诗句》;1925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27年参与贡戈拉逝世三百年祭的活动,并将其长诗《孤独》改写成散文体。192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贡戈拉的句法演化》,并于1935年将该论文扩写成文学专著《贡戈拉的诗歌语言》。
需要指出的是,当先锋派诗歌破土萌芽,当他的“二七年一代”的伙伴们争先恐后地致力于诗歌创作的时候,当贡戈拉的影响重新振兴的时候,甚至在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达马索·阿隆索沉默了二十年,直至1944年才又出版了《暗淡的消息》和《愤怒之子》。后来的诗作主要有《人与上帝》(1955)、《视觉享受》(1981)和《对上帝的疑和爱》(1985)。
西班牙内战前,他曾在巴伦西亚大学任教授。战后,他在马德里大学任罗曼语文学教授,曾在皮达尔领导的历史研究中心工作;曾任《西班牙文学》杂志社社长。1948年起任皇家学院院士,并于1968—1982年任院长。他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是欧美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1978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90年在马德里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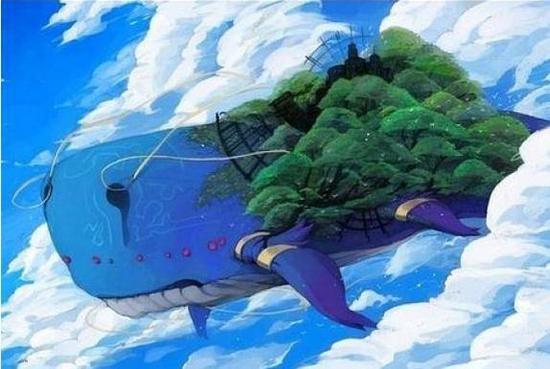
达马索·阿隆索算不上多产诗人,但却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为西班牙古典诗歌(尤其是“黄金世纪”)与当代诗歌的研究做出了不懈努力与杰出贡献,在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942)、《梅特拉诺的生平与著作》(1948—1958)、《西班牙诗歌》(1950)、《西班牙当代诗歌》(1952)、《文学评论家梅嫩德斯·佩拉约》(1956)、《从黑暗时代到黄金世纪》(1958)、《黄金世纪的两个西班牙人》(1960)、《四个西班牙人》(1962)等。此外,他还翻译了乔伊斯、霍普金斯、艾略特等英国诗人的作品。
达马索·阿隆索的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诗作主要是《纯诗:城市小诗》(1921)和《风与诗句》(1924)。这些诗作与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作品相仿,具有先锋派的特征。这是一些轻快活泼、热情洋溢的小品,描绘了年轻人天真烂漫的心灵和品格,不时显露出未来主义的叛逆与讽刺的锋芒。如下面这首题为《她是怎样的》的十四行诗:
门,洞开。轻盈温柔地到来。
既非物质也非精神。携带着
航船轻微的摇晃
和晴朗一天的晨光。
不是和谐也不是色彩。
心里明白,但是
却说不出话,因为她
非形体,形体也容纳不下。
语言,平凡的泥土,未开刃的凿子,
将这理念的完美之花
置于我的婚礼明亮的夜晚
并温和、谦虚地歌唱
感觉、阴影、事件,
当“她”将我的心充满。
在这首诗的前面,阿隆索引用了希梅内斯的一句诗:“我的上帝,他是怎样的?”这句诗引自“心灵的十四行诗”(《转瞬间的回归》)。笔者认为,无论是希梅内斯的“上帝”,还是阿隆索诗中的“她”,指的都是诗神缪斯。两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可以看出,在阿隆索诗歌创作的初期,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希梅内斯的影响。因此,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纯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西班牙内战结束以后,从1940至1945年是阿隆索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作品有《暗淡的消息》和《愤怒之子》,后一部尤为重要。应当指出,这是与作者早期诗歌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暗淡的消息》包括16首诗,作于20世纪40年代,包括纪念加西亚·洛尔卡的挽歌和另一首更为平静也更为隐秘的《巨大或泪水的源泉》。后者的题目取自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思想(当时他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位神秘主义大师认为:创造物只表达了造物主不完美的信息。诗中既有对人生的热爱,也有对不幸命运的谴责,表现了人生在世的苦闷。
《愤怒之子》(1944)是阿隆索的代表作,包括25首诗作,大多作于1942至1943年。在西班牙战后诗坛上,无论对佛朗哥政权所提倡的还是所打击的诗学理念,阿隆索的诗歌都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因此,有人称其为“1944年革命”。西班牙内战以后,留在国内的“二七年一代”的诗人有三位: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赫拉尔多·迭戈和达马索·阿隆索。与前两位的诗作不同,《愤怒之子》不逃避现实,不保持沉默,犹如一声声呐喊,将痛苦尽情地宣泄出来。在20世纪50年代,阿隆索本人曾将《愤怒之子》置于“拔根派诗歌”之列。他说:
世界对我们是一塌糊涂,是一种苦闷,而诗歌是一种对秩序和锚的狂热的寻找……我们四处回眸,觉得自己像一个难以辨认的妖魔,被另一群如此不可理喻、如此残忍抑或像我们一样不幸的妖魔包围……要么我们看到了许多尸体,在数以百万计的活的尸体中间,所有的都在腐烂,堆积如山,可作为我们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草的腐殖质,要么我们看到了世界末日,地球已变成荒漠,仇恨与不公正,入侵的毒根,将扼杀并毁灭全部的爱即全部生命。我们在黑夜中漫长地呻吟。我们不知向何处呐喊。
这就是为什么达马索·阿隆索将该书命名为《愤怒之子》。这是一部“抗议和探究之书”,既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更表达了其对非正义的愤恨。在该诗集中有一首题为《拿油壶的女人》的诗,168行,通过对一位普通劳动妇女的刻画,体现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黑暗,也表达了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关注和同情。请看这首诗的片段:
此时几乎是黑夜,
拿油壶的妇女
在人行道上拖着身躯
要去哪里?
请靠近些:她看不见我们。
与她双眸那寒冷的铁相比,
与裹着她的脖子和头颅的
暗淡的披肩相比,
与她灵魂中荒凉的景色相比,
我不知还有什么更灰色的东西。
她慢慢地走着,拖着双脚,
消耗着地面,磨损着鞋底,
但总是被一种黑暗的恐惧,
一种逃避厄运的意志
向前拖去。
……
啊,对了,我认识她。
我认识这个女人:她从火车上来。
一列长长的火车,
她走了好多个白天,
好多个夜晚:
有时冒着大雪、严寒,
有时阳光灿烂,
风儿摇动着年轻的灌木,
田野上燃烧着奇异的花
一朵朵爆炸,连绵不断。
她走啊,走啊,
喧哗声、车轮声、
陈旧的尼古丁味,火车的煤烟,
常使她头晕目眩。
啊!
白天和夜晚,
夜晚和白天,
白天和夜晚,
夜晚和白天。
但可怕的火车
停在那么多不同的车站,
可她不清楚站名,
不知道地点,
也不知道时间。
……
《愤怒之子》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突破。作者用深刻的人性来反对单纯的表诉衷情和唯美主义,使用罕见的、反诗歌的语言以对抗当时流行的矫揉造作,用自由体对抗加尔西拉索派提倡的传统的十四行诗。
从1955年起,是达马索·阿隆索诗歌创作的第三个时期,作品主要有《人与上帝》(1955)、《视觉的享受》(1981)和《对上帝的疑和爱》(1985)。在《人与上帝》中,愤怒已然消失,诗人平和、冷静地分析和探讨人与神的古老关系。微观与宏观相互制约,理智与爱意相互纠缠,总之,诗人在探求关于生命价值这一永恒命题的答案。
在“二七年一代”的成员中,达马索·阿隆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学者和诗歌评论家。
作者简介

赵振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长。著作有《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拉丁美洲文学史》《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詩·革命》《拉丁美洲文学大花园》《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西班牙语国家卷》等,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当代女性诗选》以及达里奥、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巴略霍、帕斯、赫尔曼、加西亚·洛尔卡、马查多、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阿尔贝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的诗集,并与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译了西文版《红楼梦》。曾获西班牙伊莎贝尔女王勋章、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阿根廷共和国五月骑士勋章、智利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2009年获中坤国际诗歌翻译奖,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本文摘自
西班牙20世纪诗歌研究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