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冰川思享库

就如北岛在谈到诗作的翻译问题时说,一个译者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这句话用在任何译者身上都应是合适的。
撰文 | 开不败的蔷薇
茨维塔耶娃是我喜欢的诗人中少有的几个,特别是她曾经和里尔克有过书信来往,记得她曾给里尔克写信说,你再不来,我就老了。
所以在书店看到有她的诗集我想都没有就买了。其实这是我的一大毛病,看外国文学,在看之前,是一定要看看译者的,特别是诗集,一个不会写诗的人来译诗势必是译不出其中的真味的。
《除非是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就是一本被翻译搞砸了的诗集。
我开始在读这本诗集时,我开始怀疑我的审美,接着有点嘀咕,我怀疑我遇上了假的茨维塔耶娃,我甚至开始怀疑茨维塔耶娃是不是徒有其名。

▲娄自良先生译作
直到我读到其中名叫《“……我想与你同居”》这一首,我突然意识到,这一首诗的内容我似曾相识,而且曾被这首诗深深打动过。只是诗句不同了,没有以往那股子味道了。
我上网搜了一下,大悟,原来这就是那首《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我这才想到看译者,我买的这本诗集译者是娄自良,而我看到的,以及无数次打动我的这首诗的译者是谷羽。
可是我纳闷了,虽然我对译者娄自良不熟悉,但总觉这个名字很熟,应该是翻译了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一位大家。
我担心自己无意中伤了一位大师,上网搜了一下,找到了云也退写的《娄自良先生记》。
看这篇文章开头我首先被娄老先生一头茂密的灰白色头发吸引,接着被他对待读者的方式所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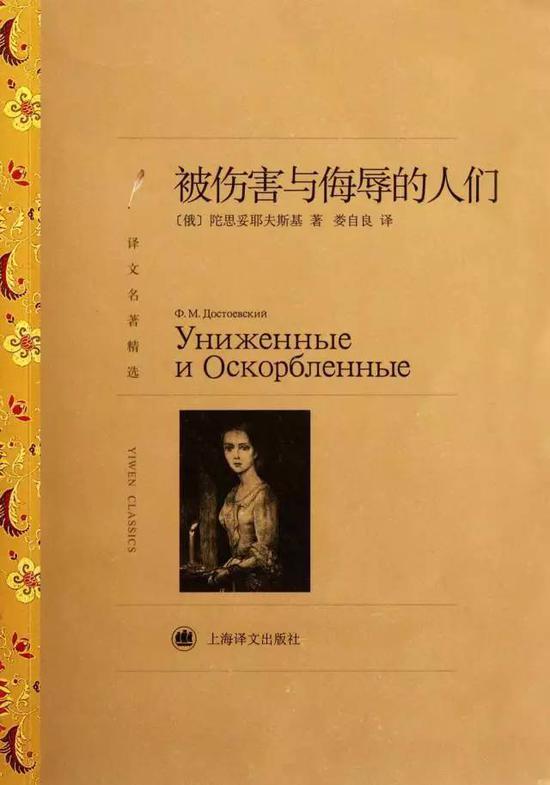
▲娄自良先生译作
2009年夏天,云也退拿着娄自良1991年翻译的《温柔的幻影》去找他,那时娄老先生77岁。照这样算来,娄老先生今年应该已经是85岁高龄了。
云也退跟他告别时,开始,他只是指了指车站的方向 “就听他在身后高声喊我。我转身,只见他大步往我这里跑来,跑中还带着有弹性的跳跃,以减缓膝盖的压力。‘我还是带你去吧,’他说。”
“大声喊我”、“大步往我这里跑来”太形象了,我一下爱上了这位老先生。
从这篇文章我还了解到,娄老先生翻译的《战争与和平》远高于他人。当然,我并没有作过类似比较,也不记得我看的版本是谁翻译的了。

▲茨维塔耶娃
可是这些并不能改变我对娄老先生译诗不如他人的看法,单从我发现的这一首来看,就不如谷羽翻译的好。光从这首诗的标题《我想与您同居》(娄自良译)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单从“同居”和“生活”两词之差,就已经决定了诗味的差异,显然用“生活”更让人感怀。
总觉得在这里,即这个语境下,用“生活”这个词有一种人生的况味在里面,而“同居”这个词则非常生硬。
“同居”是利牙咀嚼硬糖,听到的是咯嘣咯嘣的声音,而“生活”则是小米牙咀嚼精良食物,绵软悠长。
整首诗译的也是大不相同,除了还能找到茨维塔耶娃诗里想表达的想与一个人安静地生活在一个小镇外,没有一点诗的味道。
娄自良对这首诗的译文:
……我想与您同居,
在某个小镇里,
那里有永恒的黄昏
和永恒的钟鸣。
还有乡村小饭店里—
那古老的时钟
清脆的滴答声—仿佛时间在点点滴落。
傍晚,有时某处屋顶阁楼会出现一支—
长笛,
而吹长笛者本人也在窗口。
窗台上还摆放着几朵硕大的郁金香。
而您,也许甚至并不爱我……
房间中央是砌着瓷砖面的俄式火炉,
每一片瓷砖上有一幅小画;
一朵玫瑰,一颗心,一艘帆船。—
而在仅有的一扇窗外只见—
雪、雪、雪。
您会躺下—我爱您的那种模样:慵懒,
淡然、漫不经心,
偶尔响起擦火柴
刺耳的声音。
香烟燃着,又渐渐熄灭,
于是在它的一端久久地颤悠着
短小的灰色圆柱—那是烟灰。
您甚至懒得把它弹掉—
于是整支烟向火里飞去。
——《“……我想与您同居”》

我们再来看看谷羽的译作: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
古老时钟敲出的
微弱响声
像时间轻轻滴落。
有时候,在黄昏,自顶楼某个房间传来
笛声,
吹笛者倚着窗牖,
而窗口大朵郁金香。
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
在房间中央,一个磁砖砌成的炉子,
每一块磁砖上画着一幅画:
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自我们唯一的窗户张望,
雪、雪、雪。
你会躺成我喜欢的姿势:慵懒,
淡然、冷漠。
一两回点燃火柴的
刺耳声。
你香烟的火苗由旺转弱,
烟的末梢颤抖着,颤抖着
短小灰白的烟蒂—连灰烬
你都懒得弹落—香烟遂飞舞进火中。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茨维塔耶娃
娄自良译的“在某个小镇里,/那里有永恒的黄昏/和永恒的钟鸣。”这一段,我更喜欢谷羽的“在某个小镇,”虽然只少了一个“里”字,但读起来却更干脆,意义也更深远,少了一个字,却更贴近了诗人对这个小镇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的无比向往的情感。然后这一句“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将这种情感更是推进了一步。
而这首诗里,最被世人传诵的一句,可以说是这首诗的点睛之句,也是谷羽译的“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
而娄老先生显然没有关注到作者对这一句的深意,只简单译成了“而您,也许甚至并不爱我。”从而将这一句整个地掩盖在了这首诗里,也让这首诗整集淹没在茨维塔耶娃的所有诗作中。
显然,这对这首诗是不公平的。这是多少年轻的朋友在热恋季节所喜爱的诗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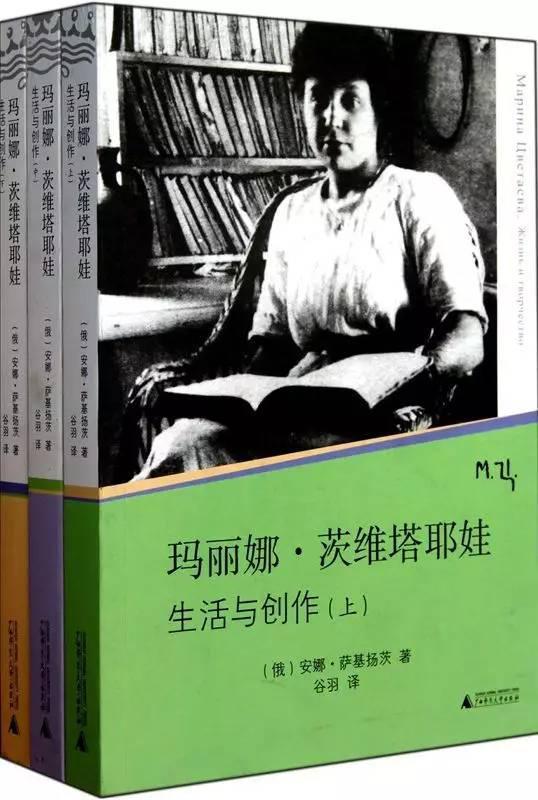
▲谷羽翻译的作品
我没看过这首诗的原文,即使看了也看不懂,但简单从阅读享受上来说,显然娄老先生译的这一首是不如谷羽先生译的。
2014年6月,《深圳晚报》曾采访过谷羽,当时他翻译的《我是凤凰,只在烈火中歌唱——茨维塔耶娃诗选》刚刚出版。介绍说,谷羽先生从1978年开始翻译俄罗斯诗歌,已经坚持了很多年。
谷羽说,他翻译诗歌有两条原则,“第一条是选择我喜欢的,我感觉能够理解、能够把握的,但是不是真正理解了,也不一定,也许理解的不准确”。“第二条,我觉得理解不了的作品,我不译,可能其他译者能够理解与把握,那就由别人去翻译。”
北岛在《时间的玫瑰》这本书的序言里说,“翻译中最难译的是声音,即音乐性和节奏(那可是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节奏呀!)。但声音也非神话,也非绝不可译,在某些难能可贵的时刻,一种声音会被神秘地倾听到并被精确地译出。”

▲谷羽翻译的茨维塔耶娃诗选
我认为在这首诗中,茨维塔耶娃蕴藏在诗里的那种向往,以及在诉说时的饱蘸情感的声音被谷羽倾听到了,并被他准确地传递了出来。这也正是这首诗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并不表示,娄老先生的译作就不好了,这只能说他没有译好茨维塔耶娃的这本诗作,或者说这本诗作中的这些首诗。
就如北岛在谈到诗作的翻译问题时说,一个译者只能译一类诗人,绝不是万能,不是通译。这句话用在任何译者身上都应是合适的。
带你读书听歌看电影

公众号ID:icereading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