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法律评论

他们是新中国民法的先驱者。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难看到当年他们有关民法理论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人可以用挑剔的目光去评论那些在崎岖的人生路上披荆斩棘备尝艰辛的先驱者。作为后来者,永远不应当忘记的是,今天我们能少走一些弯路,避免一些挫折,多取得一些成就,那都是前人呕心沥血的代价换来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当被人们遗忘。
今天是2017年清明节,谨以此文致敬与怀念新中国民法的先驱者!
本期推送转自公众号“燕大元照法律图书”2017年3月15日推送,敬请关注!
他,倾尽心力译介外国民法学重要作品
文/张谷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民法总则讲要》

谢怀栻先生(1919-2003),湖北省枣阳县人。1938年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系,1942年毕业。1948年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讲授民法、民事诉讼法。1951年到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工作,随后该院改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在该校哲学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于1988年退休。2002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终身研究员。
谢老在法学方面的造诣不仅体现在他的著述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对于外国民法学重要作品的译介中。译介工作包括直接的翻译和间接的校阅。而要译介这些外国民法学文献,光是语言就涉及英、徳、日、俄等四种外国语文。
谢老在大学毕业时,即以掌握了英、日、德三种外语,而在多年的放逐之后,对于译事,谢老居然尚能胜任愉快,其功力可见一斑。1979年之后,谢老从德文、英文将一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如海恩茨·休布纳的《德国民法中编纂法典的基本问题和当前的趋势》,格奥尔格拉茨的《匈牙利民法典的修改》以及康·茨威格特和海·克茨《比较法导论》中的一部分。
在这些零散篇什之外,谢老在1981年和2001年两度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这不仅是绝大多数民诉法学者办不到的,更是绝大多数民法学者望尘莫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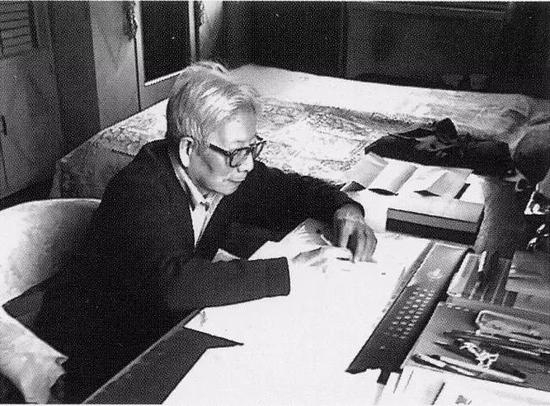
2001年,谢怀栻先生手术后伏案工作
此外,谢老还为多种重要的德、日文的翻译作品担任了译校的工作,早些年的,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近些年的则更多,如德国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罗伯特、霍恩的《德国民商法导论》以及日本民法学家我妻荣的《债权在近代法里的优越地位》。校阅者要把关,要校正译者的错误。为此谢老花了极大的精力,担任起一字一句的德文、日文的校阅工作。
2001年,谢老身患癌症,还一直坚持工作,并亲笔校对,《德国民法总则导论》(德国拉伦茨著)一书,由于多个译者文风以及用语不一致,谢老的校对工作十分困难,有许多部分,实际上是谢老重新翻译的,而且主要是在病榻旁完成的。他亲自改过的译稿往往是丹黄灿然。
谢老的俄文学习虽晚,但程度却丝毫不逊于徳文和日文。开国以后我们曾一度“以俄为师”。50年代初期,谢老先是在中央政法干校的俄文学习班上,从孙亚明先生学习俄文。
后来,谢老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的《联共(布)党史》,一本词典和一本语法书,对照《联共(布)党史》的中文翻译本,一段一段背,一本书精读之后,也就熟悉了一门语言。谢老在中央政法干校担任哲学教员,教授逻辑学,但他仍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外文法学资料。那时,他和李为共同翻译出版了前苏联A.B.维涅吉克托夫的《苏联民法对社会主义财产的保护》(法律出版社1957年8月版)。
被打成“右派”期间,谢老买来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温习俄文的材料。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格里巴诺夫和科尔涅耶夫主编的《苏联民法》的中译本,全书二十六章,谢老翻译了其中第二章至第六章。
张中行先生认为“精译”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精通外文;二是精通本国语;三是有足够的所译著作这一门类的学识;四是认真负责。《苏联民法对社会主义财产的保护》的中译本可以说符合上述四项条件,称得上是“精译”。这本著作中的很多观点对于理解1949年以后乃至当前的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都有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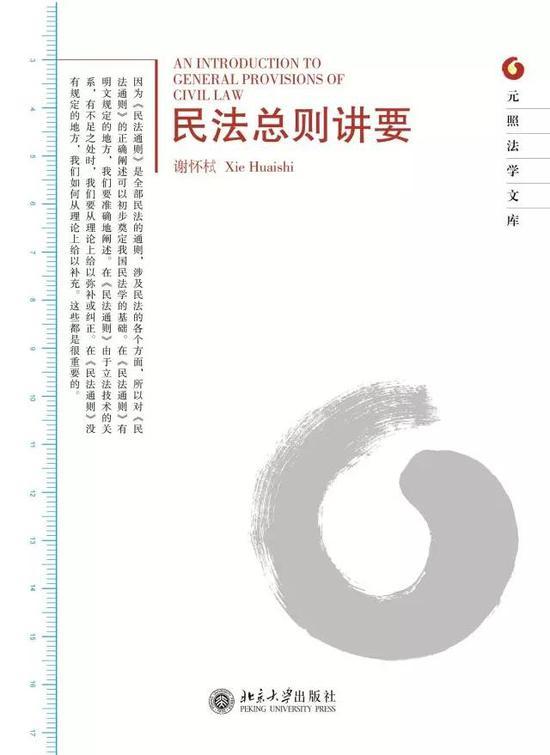
《民法总则讲要》
谢怀栻/著
“我们的民法算是真的要出来了”
文/周大伟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佟柔先生(1921-1990),我国著名民法学家,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佟柔先生执教四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已成为今日中国民法教学、研究和实践活动的中坚力量。国内民法学界公认,佟柔教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民法学的带头人,称赞他是中国民法的权威和泰斗。日本法学家称其为“中国民法之父”,美国法学家称他是“中国民法先生”。
佟柔先生一生中最高兴的事,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顺利起草和成功颁布。
1986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报审阶段。世界上的事,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就在法工委准备将民法通则草案报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同时,作为学术对立面的经济法学派也在进行紧张的“院外活动”。有消息证实,经济法学派已经迅速组成一个法案起草小组,打算起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大纲”,以便通过国务院行政渠道同时提交人大法工委讨论。有消息称,经济法大纲的起草工作小组已经进驻北京西郊的一个宾馆。鸣笛之间,一场立法的赛跑已经开始。
到底是采用民法通则,还是采用经济法大纲?最后拍板的人,并不是学者,而是官方。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法律学者,如何与政府融洽地合作,既不趋炎附势,又能让官方从谏如流,几乎是个千古难题。像佟柔教授这样的著名学者,此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已经不难,但人家听不听得进去,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这一回,以佟柔为代表的中国民法学派的声音,听上去显得格外清晰和坚定。
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在现阶段中国的立法活动中,一个法案的最后通过,往往和最高权力机构中的某一个核心人物的最终首肯直接相关。此刻,彭真委员长就是民法通则这部法律的重要推手。令人好奇的是,彭真最后是由于什么原因力推“民法通则”而断然否决了“经济法大纲”?他身边懂法律的顾问班子里究竟是哪几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是王汉斌,还是顾昂然和杨景宇?或者是自己在法工委任职的小儿子傅洋? 至今,人们似乎还不得而知。
据傅洋回忆,当时在将决定民法通则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后,经彭真建议,组织了一个阵容庞大的座谈会,邀请了一百八十多位包括法律学者以及各个实际部门在内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对《民法通则》进行讨论,以便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彭真还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行了晚宴。当时,这个宴会不单单地是一种请客吃饭,而是代表着国家对于法律工作者的最高礼遇,也是对民事立法工作的极大支持。
有人看到,就是在这个宴会上,紧靠彭真旁边就座的并不是某个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而是一介布衣的学者佟柔,而且还看见彭真在给佟柔教授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多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的感觉。
会后,我亲眼看到佟柔老师拉着中国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专家、安徽大学法律系教授周枏的手说:“周老哥,这回我们的民法算是真的要出来了。”周枏老先生一边眯着眼笑,一边不住地点头。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民法通则》明确地把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通则》的颁布,使人们在民法和经济法相互关系问题上的认识逐步趋于统一。
据我个人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当初整个《民法通则》的制定和颁布过程,自始至终都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一群学者的执著坚守、一次对立学派的绝地反击、一位领导人的重要指示,然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的偃旗息鼓。
《民法通则》终于正式颁布了。1986年前后的那段时间,可能是佟老师一生中最忙碌和最高兴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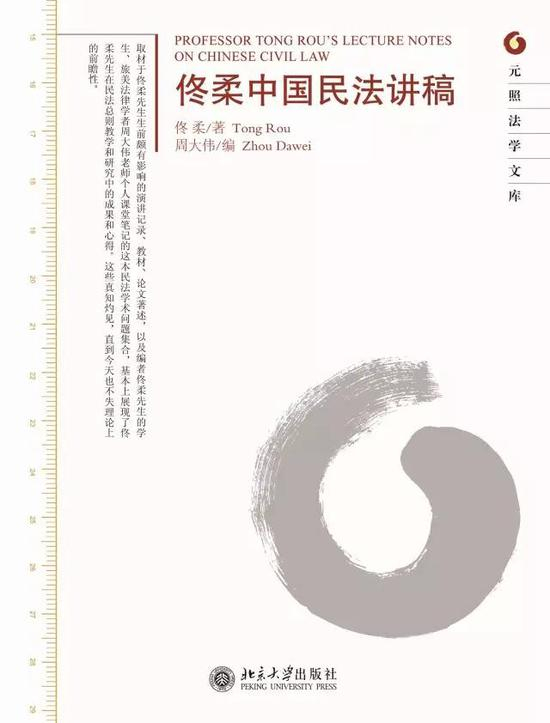
《佟柔中国民法讲稿》
佟柔/著 周大伟/编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