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志峰评论
连传销组织都不要你,你还有脸吃?
乔志峰
这两天,有个新闻在网上刷屏了:青年误入传销窝点,饭量过大“惨遭遣返”。说的是湖北青年小吴致富心切,不小心被骗到广州一传销窝点,小吴无奈只好暂时妥协。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小吴没能成功拉到一个下线。没有任何业绩也就罢了,偏偏小吴又是个食欲好、饭量惊人的小伙子!这让传销窝点的小头目很是光火:人笨也就算了,还这么能吃,这样的人不能留!他们一商量,将小吴痛打了一顿,赶出了窝点。
进了传销窝,想跑出来恢复人身自由,不说“门都没有”,起码没那么容易。要不说传销是经济邪教呢,实施人身控制那是相当专业的,没收手机、钱包、身份证不说,24小时有人贴身跟随,连上厕所都被盯得死死的,不给你留任何机会。为了脱身,有人从楼上往下扔写求救信息的钞票,有人甚至不惜抽空子直接跳楼……运气好的获救,运气不好的换来传销组织更严密的看管和更悲惨的毒打。可是,可是,这位湖北青年小吴,竟然被传销组织主动给“遣返”了,不为别的,只因为他的一个特长——能吃,特别能吃!唉,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哪。

新闻的情节其实并不新鲜,很多年前就出现过类似的段子,说某人被传销组织骗去了,眼看出不去,他就既来之、则安之,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传销组织很快就发现他的几大“特色”,一是饭量大如牛,二是上课就打呼噜,三是下课立马精神焕发跟吃了春药似的使劲调戏女学员。头目忍无可忍,最后一跺脚:算老子栽了,送他走!传销组织也不养闲人,更不养好吃懒做调戏妇女的二流子啊。
相对而言,段子当然更精彩、更搞笑。可段子毕竟是段子,是编造出来娱乐的。当段子有了现实版,那可是真人真事儿,不得不让人感叹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某些人做不到。假如这位湖北青年小吴趁机开个直播啥的,说不定真能因祸得福、一夜走红,混个网红当当哩。
术业有专攻、闻道有先后,天生我材必有用,能吃也是救命技。不过,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连传销组织都受不了,乃至于要开除、要“遣返”的人物,那得多不招人待见啊,想找个工作得多难啊。这样说,并非对湖北青年小吴施以廉价同情或歧视,而是心有戚戚焉,想到了我自己——他只是能吃而已,老乔俺不光能吃,每顿饭还要喝酒,岂非升级版的“吃货”,更加不受待见?

说到我能吃能喝,那可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从小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分。我是70后,小时候生活在农村,物质资源匮乏,能吃饱饭就算很幸运了。小孩子经常住姥姥家,似乎是一种习惯,我也不例外。姥姥养了几只下蛋母鸡,每天将鸡蛋小心收起,攒一段时间就带到集市上,换点油盐酱醋和生活用品,因此对鸡下了几个蛋特别上心。忽然有一天,她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感觉鸡最近下蛋少了。这不应该呀,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是被黄鼠狼给叼走了,还是被谁给顺手牵羊拿走啦?
于是乎,她老人家就留了心,有空就躲在暗处观察鸡窝周边的动静。这一留神不打紧,她看到了令她目瞪口呆、终生难忘、在其有生之年反复絮叨了足有一万遍的神奇一幕——
母鸡这边刚“咯咯哒”下完蛋,一个光屁股小孩就出现了,径直走到鸡窝边捡起尚且发烫的鸡蛋,用一根大铁钉“咔”地一下打破,放到嘴边哧溜哧溜几口吸个精光。整个动作当真是一气呵成,就如行云流水一般纯熟,一看就是“惯犯”。鸡蛋丢失的原因,终于真相大白。
那光屁股小孩,当然就是区区在下。发现了这个秘密,家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当时也就三、四岁的样子,从未有人教我吃生鸡蛋,我是怎么学会的呢?后来,老人们给出了一个非常玄乎的解释:我从小身体瘦弱,胳膊腿儿细得就跟麻杆似的,老祖宗们(指去世的老人)看着心疼,就冥冥中给我指点了个喝生鸡蛋补身子的法儿。从这档子事儿可以看出,我贪吃贪喝那是与生俱来的,并且跟柳三变“奉旨填词”一样,那是奉了老祖宗们的“指示”、为了延续香火才吃才喝的,因此吃得理直气壮、不容他人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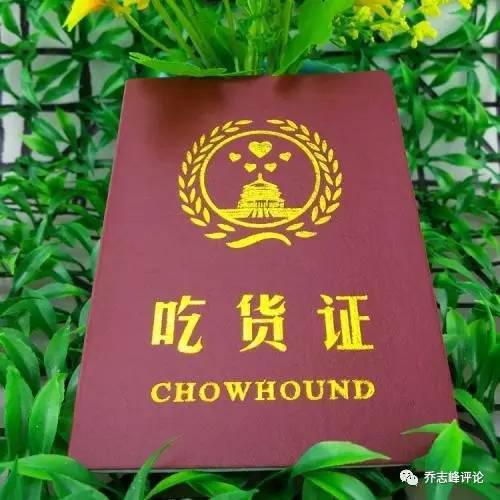
可惜,我就吃了大概半年的生鸡蛋,后来就再也不吃了。直到现在,我自己都想不通生鸡蛋是如何下咽的。随着年龄渐长,生鸡蛋是不喝了,但作为一枚合格的吃货,我很快就学会了另一门“手艺”——喝酒。早茶晚酒,成了我现如今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既然说起喝酒,不妨说点鄙人喝酒的趣事为大伙儿下酒。
在省城上学那会儿,我跟一位年龄比我大7岁的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他是先上了高中,没考上学,就回家种地了。这不能怪他不努力,当年想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不跟现在这样,只要多少考几分,就能找个学校上。种了几年地,发现实在太辛苦,受不了,还是必须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所以又回高中继续奋战,所以比我这样正常年龄的学生大了不少。也正因他年龄大、“混过社会”,所以既会喝酒又会划拳。我们一见如故,就一起吃饭,馋了就弄点酒喝。大家都穷,也没啥钱,基本上就是买包辣辣的油炸花生,就着喝。
有一回,两人又馋了,就去小卖部买花生,可小卖部没开门。这可咋整啊?这时看到路边有人卖大萝卜,灵机一动买了俩。然后两人一人攥着个萝卜,咬一口萝卜就一口酒,不大会儿就飘飘然起来。后来有再好的下酒菜,也再也找不回当初就萝卜喝酒的那份快意和感觉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喝酒就难免喝醉,喝醉就难免出丑。我之前写过一篇《那些年喝酒出过的丑》,已经如数家珍地列举了不少我喝酒的“光辉事迹”,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有湖北青年小吴和我这样的吃货“负面典型”,当然也就有“正面典型”。比如作家三毛。荷西问三毛:你想嫁个什么样的人? 三毛说:看的顺眼,千万富翁也嫁。看的不顺眼,亿万富翁也嫁。 荷西就说:那说来说去你还是想嫁个有钱的。三毛看了荷西一眼说:也有例外的时候。 “那你要是嫁给我呢?”荷西问道。 三毛叹了口气说:要是你的话那只要够吃饭的钱就够了。“那你吃的多吗?”荷西问道。“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三毛小心地说道。就这样,三毛终于顺利地把自己嫁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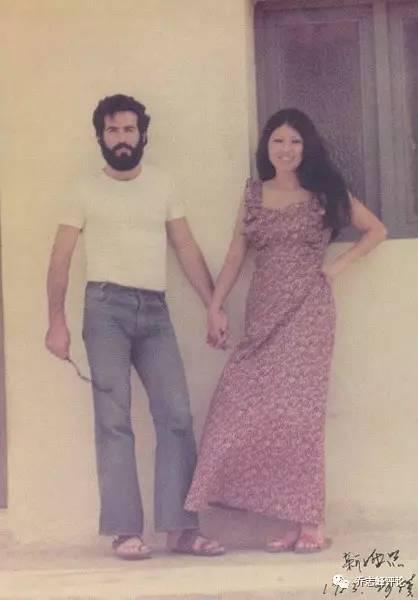
对三毛“吃得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一点”的高尚情操和高度自制力,我佩服得紧,却自问学不来。在吃喝方面,我最佩服的,乃是“陈也罢”。“陈也罢”既是名人,也是大官,他老人家玩的幺蛾子才多呢。
“陈也罢”是谁?不是现代人,是明朝人,成化年间的翰林编修。在古代,翰林一向被人们视为最有学问的人,甚至是“文曲星下凡”。可这位陈翰林,却并非给人一种才高八斗、精明能干的印象,反倒有那么一点稀里糊涂,特别是他对很多事情都不介怀,经常把“也罢”二字挂在嘴边,以至于被人送了个“陈也罢”的绰号,朝野乃至民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虽然明朝那时候还没有“吃货”这个词儿,但毫无疑问的是,自古以来都不缺少“吃货”群体。毕竟民以食为天,上至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只要还食人间烟火,鲜有不贪口腹之欲者。吃点喝点,对谁都是一种享受。可当年还不像现如今这般“物质极大丰富”,哪怕是朝中为官,也不一定总能锦衣玉食,更何况翰林还属于“清要之职”,听起来高高在上,其实清水衙门油水不大。“陈也罢”日子清苦未必,可顿顿生猛海鲜、进口牛扒、茅台拉菲,却也不大可能。怎样才能大快朵颐、山吃海喝一通,还不必担公款吃喝之责呢?去有钱人家里蹭饭,就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了。
话说当时与“陈也罢”同朝为官者当中,有两个人重名了,都叫杨文卿。一个是浙江人,担任刑部郎中;另一个是山西人,官居户部郎中。刑部、户部,都是有权有钱的单位,比翰林肯定要富裕。有一天晚上,浙江的杨文卿请“陈也罢”吃饭,“陈也罢”却一溜小跑跑到了山西杨文卿的府上。
人家都已经上床睡觉了,听说陈翰林来了,赶紧起身接入。两人对坐聊天,主人心里奇怪啊,不知道“陈也罢”前来所为何事。闲聊几句,“陈也罢”做出一副很随意的样子,呵呵笑道:老兄请客,也别搞得太隆重啦,咱弟兄们谁跟谁呀,有一杯小酒、一把豆子,多少再弄点肉,就凑合啦。主人不由愕然,可也不好意思回绝,只好吩咐家人备上酒饭,“陈也罢”自然大快朵颐、乐不可支。
那边浙江杨文卿左等右等,不见“陈也罢”前来,派人前往探问,才知道“陈也罢”跑山西杨文卿家去了,于是追到了山西杨文卿家。“陈也罢”这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连称搞错了。于是乎,在山西杨文卿府上蹭了一顿饭,原本要请客的浙江杨文卿那一顿饭也自然省不得。这就叫“一人请客、两家吃饭”,谁让你们的名字一模一样,被“陈也罢”给钻了空子呢。
“陈也罢”蹭饭的本事那是相当的有名,连冯梦龙都对其多有耳闻。在冯梦龙的笔记小说《古今谭概》中,也记载了“陈也罢”的一件趣事。一天,“陈也罢”跑到一位官员家,到饭点了也不走。主人只好询问:陈翰林,您老今天大驾光临,有何见教啊?“陈也罢”眼一翻:你不是请我喝酒吗,为何还来问我?主人很惊讶,可除了准备酒菜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后来,终于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家主人去年曾发请帖请“陈也罢”吃饭,“陈也罢”今年翻检旧书信,又翻出那张请帖,就按请柬里写的日期再次赴约,也就是把旧约当新邀,去年吃了一顿,今年又去吃了一顿。在记叙了这件事情之后,冯梦龙不由得感叹道:以后请这样的人吃饭,只能口头邀请,千万不能发请帖。否则,他把请帖保存起来,还不每年的这一天都跑来蹭一顿饭啊。
蹭饭能蹭得像“陈也罢”这般煞费苦心、这般花样百出,倒也并不令人讨厌,里里外外还透着几分可爱。不知今天的诸多吃货们,能否从古圣先贤的事迹中得到启发,生出蹭饭当学“陈也罢”的想法来呢?
看看,说到吃、说到喝,我竟然满嘴跑火车、大放厥词,有点刹不住车了。好啦,不扯闲篇了,有人请我喝酒,得早点去,争取占个夹菜方便的好座位。如果有人问:连传销组织都不要你,你还有脸吃?我的回答是:为啥不能吃?传销那种龌龊事儿咱不沾不碰,吃点喝点无伤大雅,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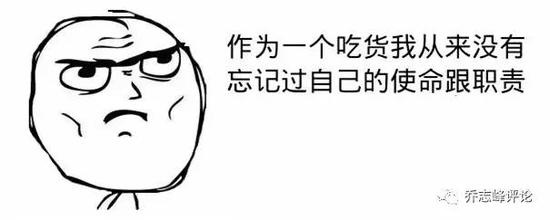
来源:乔志峰评论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查看原文

